來源:中國少年報(bào)·未來網(wǎng)2025-08-20
編者的話: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。
今年7月7日,在百團(tuán)大戰(zhàn)紀(jì)念館,習(xí)近平總書記對(duì)前來參觀的青少年學(xué)生和紀(jì)念館工作人員深情地說:“廣大青少年生逢其時(shí),要賡續(xù)紅色血脈,樹立強(qiáng)國有我的遠(yuǎn)大志向,做堂堂正正、光榮自豪的中國人,勇?lián)褡鍙?fù)興的時(shí)代大任。”
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,偉大抗戰(zhàn)精神如同不滅的星火,照亮億萬少年兒童成長之路。即日起,中國少年報(bào)·未來網(wǎng)以“我家的抗戰(zhàn)先輩”為主題,推出全媒體報(bào)道,邀請(qǐng)抗戰(zhàn)英烈、英模等的后代來講述、追憶在那段崢嶸歲月中先輩們?yōu)槊褡濯?dú)立、人民解放拋頭顱、灑熱血,抗日救亡的英勇事跡,引領(lǐng)廣大少年兒童傳承弘揚(yáng)偉大抗戰(zhàn)精神,爭做愛黨愛國、勤奮好學(xué)、全面發(fā)展的新時(shí)代好少年。
“我的祖籍山東泰安,家中長輩有多人參加八路軍。祖父陳國良是抗戰(zhàn)時(shí)期津浦鐵路線上有名的偵察英雄,綽號(hào)‘夜貓子’:伯父在吉山戰(zhàn)斗中,為保護(hù)密碼本,險(xiǎn)些喪命于日軍的刺刀之下……這些故事聽了幾十年,就像刻在腦子里。”坐在堆滿史料的書桌前,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(xué)院研究員、著名軍史研究專家陳宇向中國少年報(bào)·未來網(wǎng)記者悉數(shù)起祖輩們的抗戰(zhàn)往事。
出生在軍隊(duì)大院,陳宇自小聽著祖輩、父輩們的從軍故事長大。后來,19歲的他也穿上軍裝,三次奔赴戰(zhàn)場,親眼看見了很多戰(zhàn)友的犧牲。那些在炮火中倒下的年輕面孔,總讓他想起祖父和伯父在戰(zhàn)場上面對(duì)敵人冰冷刺刀時(shí)的決絕——原來,先輩們寧死不屈、血戰(zhàn)到底的抗戰(zhàn)精神,早就在家族血脈里扎了根。
在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前夕,循著陳宇的回溯,我們得以翻開這段藏在家族記憶里的抗戰(zhàn)史:那是面對(duì)刀槍時(shí)的敢打敢拼與智勇較量,也是一次次戰(zhàn)斗中的生死堅(jiān)守,更是一個(gè)民族在危難時(shí)刻絕不低頭的脊梁。
夜襲據(jù)點(diǎn)“死里逃生”
我的爺爺陳國良,1906年生在山東泰安的大汶河邊上。家中長輩總說,祖父是“村里少有的文化人”。他讀過私塾,高小畢業(yè)——在那個(gè)年代的山東農(nóng)村,這就算“有學(xué)問”了。他記性特別好,《四書五經(jīng)》能背得滾瓜爛熟,以至于后來大姑的過目不忘的本事,總被說“隨她爹”。
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后,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。當(dāng)年12月,日軍占領(lǐng)泰安城,燒殺搶掠的消息傳到村里,村民們都攥緊了鋤頭。轉(zhuǎn)年開春,村里來了八路軍,說要打鬼子,我祖父二話沒說就報(bào)了名。后來,他成為八路軍山東縱隊(duì)魯中軍區(qū)交通隊(duì)的一名偵察員,主要在津浦鐵路沿線跑情報(bào)。
那時(shí)候八路軍山東縱隊(duì)缺槍啊,除了鄉(xiāng)親們捐的打獵用的土槍外,幾乎沒別的家伙事兒,只能從鬼子手里奪。祖父所在的交通隊(duì)名義上是傳情報(bào),實(shí)際上還兼著“運(yùn)輸隊(duì)”的活兒,瞅準(zhǔn)機(jī)會(huì)摸進(jìn)日軍據(jù)點(diǎn),繳槍、拿子彈,回來武裝游擊隊(duì)。
祖父經(jīng)常接到組織上分派的傳遞情報(bào)任務(wù),到沂蒙山八路軍抗日根據(jù)地,到地下黨和游擊隊(duì)所在地濟(jì)南、濟(jì)寧、曲阜、棗莊、臨沂、徐州等地傳送情報(bào)。戰(zhàn)友們稱他是“飛毛腿”,從泰安附近出發(fā),到濟(jì)南、曲阜常常是一天多走個(gè)來回。回來的路上,祖父還經(jīng)常捎帶著襲擊日偽據(jù)點(diǎn),帶幾支槍回來。
1938年12月的那次夜襲,泰安以南的華豐鎮(zhèn)日軍據(jù)點(diǎn)駐著百十來個(gè)日軍,祖父摸清楚他們換崗的空當(dāng),夜襲潛入繳獲手槍8支。后來鬼子發(fā)現(xiàn)槍沒了,知道是他干的,貼出告示懸賞抓捕他,那時(shí)沒有照片,只有畫像,大概是畫技不太好,濃彩重筆,畫得倒像只貓頭鷹(山東人叫“夜貓子”),祖父的另一綽號(hào)就這么傳開了。

位于山東泰安陳美莊的日軍據(jù)點(diǎn)舊址
最險(xiǎn)的一次,是1940年初從日軍的“魔掌”中“死里逃生”。祖父與同時(shí)被捕的一名八路軍戰(zhàn)士被關(guān)在日軍陳美莊據(jù)點(diǎn)的“芋頭井子”(泰安方言,俗稱“地窨子”,冬天儲(chǔ)存紅薯所用)里,次日將被槍斃。當(dāng)晚深夜,祖父讓戰(zhàn)友托住雙腳,用頭頂和肩膀磨開地窨子頂部的碾盤,兩人逃生后將碾盤復(fù)位。待日軍次日發(fā)現(xiàn)兩人逃跑后,竟傳言他們會(huì)“土遁”。
其實(shí)哪有什么法術(shù),就是硬拼著一股子活命的勁兒。后來聽家中長輩說起,祖父回家養(yǎng)傷時(shí),半個(gè)腦袋的頭發(fā)都磨沒了,露出白森森的頭骨,很長時(shí)間才長出頭發(fā)來。在后來的一次被捕中,祖父就沒有那么幸運(yùn)能逃走了。1941年3月犧牲時(shí),年僅35歲。
吉山戰(zhàn)斗里的“生死場”
祖父犧牲一年后,1942年的吉山戰(zhàn)斗,成了伯父陳成彥的“生死場”。那時(shí),日軍為了摧垮山東抗日根據(jù)地,進(jìn)行了一次次瘋狂的大“掃蕩”。據(jù)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院數(shù)據(jù)記載,1941年至1942年,日偽軍千人以上的“掃蕩”增加到70余次,其中萬人以上的“掃蕩”就有9次,小規(guī)模的“掃蕩”幾乎每天都有。
到了1942年秋,形勢愈發(fā)嚴(yán)峻,日偽軍集結(jié)1.2萬人對(duì)沂蒙山區(qū)進(jìn)行“鐵壁合圍”式大掃蕩。10月17日拂曉,日偽軍分?jǐn)?shù)路向萊北山區(qū)拉網(wǎng)合圍,駐茶葉口一帶的泰山區(qū)黨政軍機(jī)關(guān)遭敵合圍,中共泰山區(qū)地委書記兼軍分區(qū)政委汪洋率地委軍分區(qū)機(jī)關(guān)一部教導(dǎo)隊(duì)突圍,在吉山遭日軍伏擊。我的伯父時(shí)任中共泰山區(qū)地委機(jī)關(guān)機(jī)要科科長,也在這支隊(duì)伍里。
伯父曾向我親述過突圍時(shí)的場面:吉山腳下槍炮聲大作,連成一片。路兩邊山上的制高點(diǎn)已經(jīng)被敵人控制,隊(duì)伍幾次沖鋒都被壓回來,激戰(zhàn)一個(gè)多小時(shí)后傷亡慘重,只能分散突圍。伯父所在的機(jī)要科接到死命令:“守護(hù)密碼本,徹底毀壞電臺(tái)后再撤退。”
那時(shí),伯父和兩個(gè)戰(zhàn)友已經(jīng)慌不擇路,三人躲進(jìn)一塊“T”字形石板下面。這塊石板豎的有3米高,橫的那塊像屋檐一樣,斜斜地遮在上頭。他們緊緊貼著青灰色的石板,大氣都不敢出,身上的衣服顏色跟山石差不多,遠(yuǎn)遠(yuǎn)看去,就跟石頭融為一體了。而就在200米外的大路上,日軍列隊(duì)走過,有個(gè)牽著白馬的日本兵,走到石板附近的時(shí)候,腳下一滑,差點(diǎn)摔了個(gè)跟頭,他抬頭看了看,卻壓根沒發(fā)現(xiàn)藏在石板下的三個(gè)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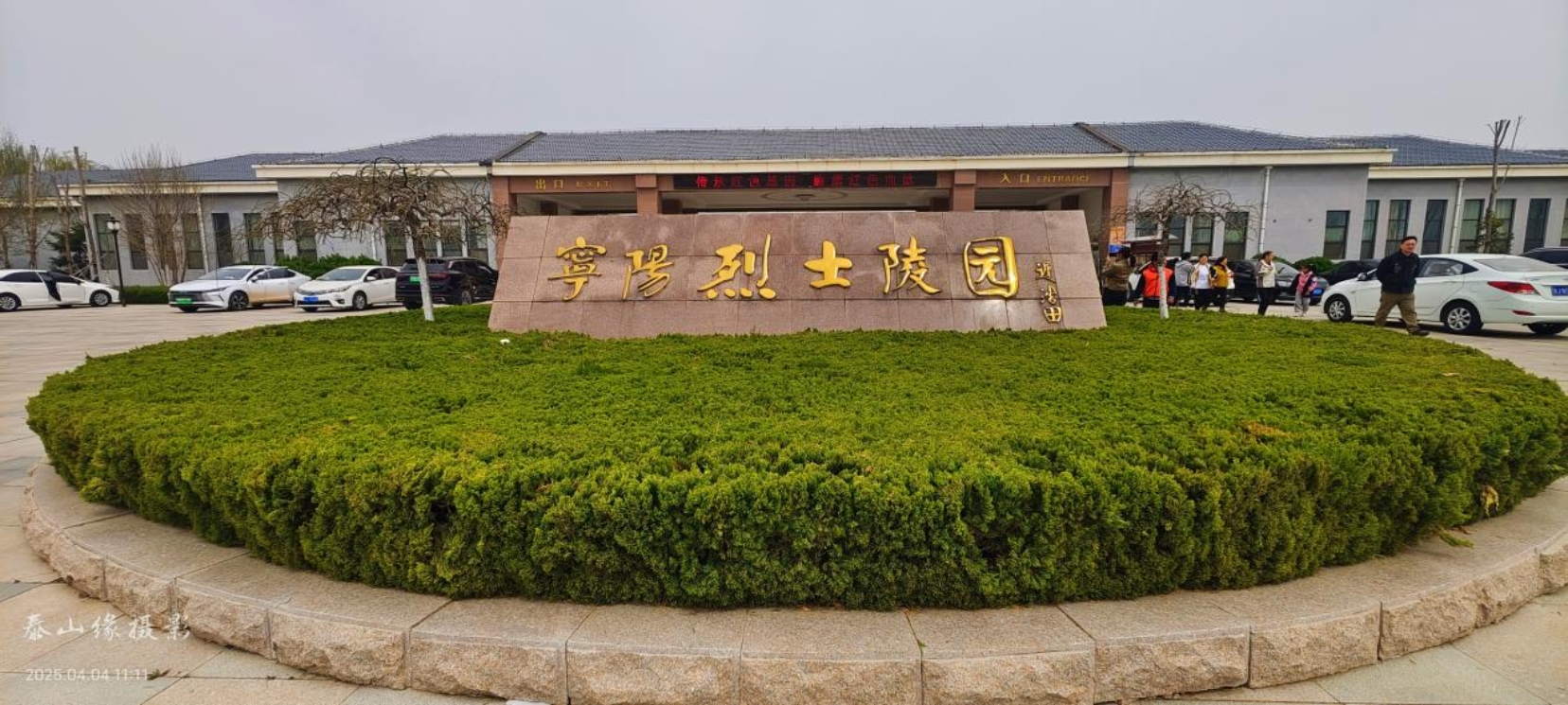
陳宇家鄉(xiāng)的烈士陵園
最險(xiǎn)時(shí),兩個(gè)日軍抬著傷員,在離他們50米遠(yuǎn)的地方歇腳。伯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他緊緊握著懷里的手榴彈,胸前的密碼本被汗水浸得透濕,后背也全是汗。那時(shí)候,他心里就一個(gè)念頭:“敵人要是發(fā)現(xiàn)了,就拉響手榴彈炸毀密碼本,與敵人同歸于盡!”三人像“木偶”一樣緊貼在石板上,不敢動(dòng)一下。直到確定敵人都走了,才敢小心翼翼地鉆出來。
剛經(jīng)歷過廝殺的戰(zhàn)場上,空氣中全是硝煙和焦煳味,聞著讓人發(fā)嘔。次日,伯父才得知,在吉山戰(zhàn)斗中,汪洋政委等323名指戰(zhàn)員壯烈犧牲,自己成為少數(shù)幸存者之一。
這只是伯父在戰(zhàn)場上面臨的“生死劫”之一。還有一次與日軍作戰(zhàn)后,伯父藏在戰(zhàn)友遺體下靜躺著裝死,清晰地聽見鬼子打掃戰(zhàn)場時(shí)拿起刺刀一刀刀刺向戰(zhàn)友遺體的聲音。那時(shí),掩藏在戰(zhàn)友遺體下的伯父大氣不敢出,聽著敵人的皮靴聲從頭上踩過,盡管最終幸免于難,但右腮遭敵人的刺刀劃開一道長約7厘米的傷疤。
年少時(shí),總見伯父拉高衣領(lǐng)以掩蓋這塊刀疤,家里人卻叫它“光榮疤”。1995年伯父病逝后,這些往事也就偶爾在同族兄弟姐妹及晚輩之間談起,連同吉山戰(zhàn)斗中的一幕幕“生死場”一道,深深嵌在我的心底。
刻進(jìn)血脈里的家國魂
從我祖父那輩算起,我家三代從軍。我的父親也深受家庭和時(shí)代的感召,很早就投身革命洪流。在我4歲那年,他為國捐軀。印象中,只記得他戴著大蓋帽、穿著軍裝,出門那一剎那的背影……這是父親生前留給我的最后一幅畫面。
穿上軍裝,于我而言是刻在骨子里的選擇。1976年底,19歲的我穿上軍裝,光榮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。那一刻,祖輩、父輩們的期許,都化作了肩上的重量。軍旅生涯中,我參加過3次作戰(zhàn),負(fù)過傷,目睹過戰(zhàn)友的犧牲。
1979年,對(duì)越自衛(wèi)反擊戰(zhàn)中,子彈、炮彈彈片在耳邊飛過,眼見著戰(zhàn)友相繼倒在血泊里。那一刻,伯父的話在我的腦海中回蕩:“沖鋒時(shí)端起刺刀直向前,有正氣在,子彈都會(huì)拐彎!”我咬著牙持槍往前沖。戰(zhàn)斗時(shí)刻面臨著危險(xiǎn),但每次想到祖父、伯父、父親,他們的革命精神總是鼓舞著我為勝利而戰(zhàn),這些經(jīng)歷對(duì)我影響極大,也影響了我的一生。
我大學(xué)畢業(yè)后專心研究軍戰(zhàn)史,總覺得這樣能離祖輩、父輩們?cè)俳赝麄兯鶜v經(jīng)的戰(zhàn)場和往事。從戰(zhàn)士到研究員,我漸漸明白:所謂傳承,就是把他們沒走完的路、沒說盡的話,一筆一畫寫進(jìn)歷史里。三十多年來,我把對(duì)先輩的敬意寫進(jìn)一百多本戰(zhàn)史著作里。
在我還是戰(zhàn)士的時(shí)候就走過紅軍長征路,后來還以學(xué)者、普通人、探險(xiǎn)者等身份走過,與妻子并肩走過,到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走了十五次,每一次重走長征路都是一次心靈之旅。祖輩、父輩沒機(jī)會(huì)走完的路,我來繼續(xù)走,他們的革命精神和長征精神相通——都是為了家國拼到底,把國家放得比生命重。
我這一輩子,踐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的古訓(xùn),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,今天的太平日子,是革命先輩們用命換來的。打個(gè)比喻來說,個(gè)人的事像小溪,國家和民族的事業(yè)就像大海,小溪只有流入大海才永不干涸。也就是說,只要大家都有“把國家放得比生命重”的精神,咱們中華民族就能無往而不勝。
(本文圖片均由被采訪人提供)
中國少年報(bào)·未來網(wǎng)記者 凌萌
編輯:郭超